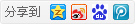“抽18元烟罚两千”的最牛村规说明了什么
一、“抽18元烟遭重罚”并不说明当地村民已分化为三六九等
村规中的等级差别并不能说明当地出现“特权阶级”
此次事件发生的所在地,在湖北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。所谓“最牛村规”,是指在今年7月22日,尧治河村出台的《尧治河村婚丧喜庆事宜管理办法》,该办法为了提倡勤俭节约,杜绝铺张浪费,规定“领导家庭(村”两委“班子成员)吸烟不得超过10元/盒,酒不得超过60元/瓶;干部家庭(企业中层副职以上干部)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吸烟不得超过5元/盒,酒不得超过50元/瓶;普通职工家庭和普通村民家庭吸烟不得超过2元/盒,酒不得超过20元/瓶。”而10月10日,村纪委、督办室联合下发了督办处罚通报,在全村对严小平、周定福通报批评,因为他们办酒席时用了接近40元一瓶的酒和18元一包的烟,并分别给予2000元的罚款。
这份村规,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烟酒的规格分成了三个档次——这又不是发工资按贡献大小区分,自己家的婚丧喜庆事宜凭什么能规定等级?这是不是反映出当地已经出现了特权阶层,已经分化为三六九等?是不是说明当地领导干部已经相对普通民众有了深入骨髓的优越感?
仅从这份规定来看,如果规定不仅仅是针对普通家庭执行的话,很难得到这样的结论——毕竟领导家庭允许的规格也不超过烟10元一盒、酒60元一瓶,这只能算非常普通的烟酒。而尧治河村是全国范围内都小有名气的“土豪村”。按村党委书记孙开林的说法,“我们这个山区的小城工农业总产值十几个亿,村民百分之百住上别墅,50%的家庭有车。”并不存在用不起好烟好酒的问题。尧治河村也不存在很严重的贫富悬殊,据孙开林称,被处罚的两家是村里条件最差的两家,“每年也有十几万的收入”。而且,这个村规也只是限定了在婚丧喜庆事宜上烟酒消费有上限,平时并不限制。
因此,村规里的等级差别,并不能说明当地出现了“特权阶级”。
这种做法也许是为了“勤俭节约”,但过于不近人情实际上侵害了村民的财产支配权
那么,这个村规的做法难道真的是为了“提倡勤俭节约,杜绝铺张浪费”?按孙开林的说法,“富裕起来后有些干部、村民开始忘乎所以。特别是近两年,铺张浪费、摆阔气的风气非常严重,天天都有人在摆宴席,比吃比喝比消费。1岁也办酒,12岁也办酒,48岁也办酒,瞅准机会就办酒。一摆就是50桌,百把桌,有的一办就是7天,想办法把送出去的人情赚回来。”“近几年没有针对摆酒的硬性规定,人情风越来越盛,每家每年送出去的礼钱超过2.5万。借着酒席赌博的风气也开始蔓延,村民们的心思都放在这个上面了,还怎么搞好生产?”
也许村规的确有治奢的考虑,但问题在于,这个村规过于严苛,不近人情。婚丧喜庆事宜对于村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事情,也是亲朋聚会的时刻,居然让普通百姓只许抽2元一盒的烟和20元一瓶的酒,即使是为了“治奢”,也太过没有道理。这实际上是侵害了民众的财产支配权,如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唐鸣所说,“对村民而言,这完全是个人行为,虽然从道德和社会风气角度应提倡节俭办理,但任何机构都不能强制其行为,更不能进行处罚。法律并没有授予村委会罚款的权力,村委会无权擅自设定处罚权。即便是该决定出台的程序合法,其内容本身也是不能侵犯村民的合法权利的。”
所以,这个村规即便是“村民代表大会通过”,也是不合法的。
那么问题来了,这个村规里的等级制既不反映现实状况,其内容又这么不近人情,目的到底是什么?
二、“最牛村规”实质反映的是明星村的“能人威权”
村书记孙开林对事件的回应,显示出的是典型的家长式威权
此事发酵后,孙开林对媒体做出了回应,从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孙开林称“国有国法,村有村规,国家政策不可能面面俱到,这就要求村民自治,通过一些手段才能治理好社会。”“我们村是集体经济,主要靠村办企业、旅游、矿山,农业的比例已经很小了。村民一般都在村里的企业上班,村里的干部基本都是村企业的负责人,家庭条件要好一些,有的村干部一年收入几十百把万,所以限制他们办酒抽10块的烟,有的村民十几万的收入,凭什么抽几十块的烟呢?所以我们是这样才分出标准的。”
从这两段话就可以看出,“最牛村规”实际上基于村民治理而出台的一个政策,所谓“治理好社会”;而村规里的等级制,实际上是因为该村是“集体经济”,如果要求干部抽10块的烟,普通村民就自然不能抽几十块的烟,隐藏的逻辑就是“否则就会乱套”。这里实质显示出的,是典型的家长式威权——村领导想要怎样的结果,村民就得遵守。
这种威权来源于“能人带领村民致富”
对于尧治河村而言,这个家长式威权的掌握者,就是村党委书记孙开林。在最近二三十年间,尧治河村由一个“贫困村”变为“土豪村”,起决定作用的,就是村党委书记孙开林。在孙开林的主导下,尧治河村开矿、修路、开发水电、开发旅游,才有了很大的变化,村民才住上了别墅,开起了小轿车。因此,对于尧治河村民而言,孙开林这种绩效带来的合法性和威望,是无比之高的。他指定的规矩,就得听,村民代表大会就得通过。尽管根本不近人情,村民私下并不想遵守。
并且,“能人威权效应”得到了正式承认
而在与尧治河村长期合作的银行看来,尧治河村之所以取得这么大成就,靠的就是“能人+银行”信贷运作模式。银行总结称:“从尧治河村的孙开林、中坪村的黄立杰、堰娅村的宦忠云、黄龙观的章祖良的身上,都能看到这些带头人都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品质好、能力强、有一颗为民办好事、办实事的‘公’心,这些村从贫穷到富裕的巨大变化表明,关键取决于带头人有眼光、有魄力、有干劲。在他们的带领下,村委领导班子不仅综合素质高,更是一个团结、向上的集体,才使全村形成一心一意抓经济、搞建设、脱贫困的局面。”银行这一总结甚至上了人民日报,对尧治河村发展的描述就是“治村能人借助金融支持创造20亿元产值”。
所谓“能人有魄力”,在银行内部总结中,给了一个更为精准的词,就叫做“能人威权效应”。在银行看来,这种“威权”是极有必要的,才能保证村子“一心一意”,而在孙开林这样的能人眼里,“我说了算”意义有多大,自然更不用说。
因此,这大概才是“最牛村规”所隐含的寓意——不管根本原因是什么,当“能人”觉得有必要管一管大家了,就出台这么一个必须遵守的规定。
三、中国村庄治理“能人模式”的隐忧
“能人”带领村民致富当然是好事,但这种人治充满危险
类似尧治河村的明星村,中国其实不少,如名噪一时的华西村、大邱庄,南街村等。许多论者早已指出,“能人政治”是让经济发展壮大的关键。绝对权威的树立,让村务管理和决策更加富有效率,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市场经济的要求,但也为明星村财富神话的破灭埋下了隐患。在明星村,权力精英往往与经济领袖存在身份重合。其控制与带领村庄所创造的财富神话,又反过来成为一种资本,巩固和强化了其在村庄事务中的绝对话语权。于是,村集体经济的舵盘完全系于少数管理人员的道德自律之上。
然而,这种自律在很多情况下被证明是极不可靠的。禹作敏锒铛入狱,乡镇企业产权不明、管理模式落后等弊病的显露,让人们看到了大邱庄脆弱的一面;而在“离共产主义只差一步”的南街村,人们在清理一位村干部遗物时,发现其私人保险柜中有两千万元以及自办的房产证等物,虽然这一消息事后被南街村管理层所否认,但相关负责人承认该村干部在外包有“二奶”。而吴宝仁领导华西村的风格,同样备受诟病。

尧治河村从“贫困村”变为了“土豪村”
与“尧治河村”临近的正面典型不少已经出了问题
对于尧治河村,在官方宣传中,不少学者已经表达了隐忧,“很多村集体的创富神话都是以‘能人’为核心的,等到‘能人’退出舞台,这么大的摊子还能否撑下去?还有,一个村集体的成功可能是以其他集体的失败为代价的,尧治河村的经验能否推而广之?”一位专家就曾如此质疑。一位银行人员也认为,尧治河村需要打造上市公司,让很多专门机构在帮助它进一步规范发展,目的是让“核心人物的威权将被慢慢削弱。”
实际上,当地宣传文件中的能人典型——中坪村的黄立杰、堰娅村的宦忠云,都已经遇到过问题。前者身兼村支部书兼任中坪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,遇到一个项目一声令下,村民就集资并同意高息举债,结果遇到了骗子损失3000万。后者则被举报致富后违规住上了500平米超大住宅,被上级政府勒令整改。而尧治河村是否也有同样风险?从类似村落的经验来看,当然也存在隐忧。